與臺積電前總法律顧問理查德·瑟斯頓(Richard Thurston)的問答
亞太地區(日本、***、中國和新加坡)占全球芯片出口的 84%,擁有 16 家半導體出口商中的 10 家和前六大供應商,其中包括臺積電 (TSMC)。這家領先的純晶圓代工廠將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在日本熊本慶祝其首家晶圓廠的落成典禮。
為什么半導體生產如此集中在東亞國家?為什么臺積電愿意組建日本合資企業,卻決定在亞利桑那州進行獨立的綠地投資,以制造先進的芯片?臺積電能否在日本第二家晶圓廠成功復制其純晶圓代工業務模式?
DIGITIMES Asia獨家專訪了RLT Global Consulting的創始人兼主要成員、Hudson Valley Fast Fab(“HVFF”)首席執行官Richard L. Thurston博士。瑟斯頓于2014年從臺積電退休,擔任高級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曾擔任臺積電的顧問,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為德州儀器(TI)與日本談判合資企業和貿易協議。
瑟斯頓博士還將與DIGITIMES顧問Albert Lin博士一起,在首屆DIGITIMES亞洲GeoWatch上分享他對日本的見解,以及它是否仍然具備在埃時代取得成功的能力論壇,定于臺北時間3月27日。
問:臺積電將在熊本開設第一家晶圓廠,并已披露第二座晶圓廠的投資計劃。據說新加坡已經重新推出了更好的激勵措施,以吸引臺積電的投資。根據您在日本的經驗和您在臺積電的工作,為什么半導體制造在亞洲這一地區如此成功?臺積電能否在日本成功復制其純代工模式?
在日本,純晶圓代工廠尚未取得成功,在日本實現這種商業模式將具有挑戰性。在韓國,三星已經能夠利用其過剩的產能做一些代工工作,但不是作為一家純粹的代工廠:它仍然主要是一家IDM。新加坡之所以有代工廠,是因為Chartered Semiconductor(被Globalfoundries收購)、UMC和SSMC(1998年臺積電與飛利浦/恩智浦的合資企業)(我在2002年至2013年期間擔任SSMC董事會成員)。但是,當然,沒有人能像臺積電那樣在純代工模式上取得成功。純粹的游戲和其他做一些鑄造工作的人是有區別的。
我于 1984 年加入德州儀器,擔任亞太區法律顧問。我們在日本、臺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經營著多家制造工廠。因此,我一直處于一個獨特的位置,可以觀察這些亞洲國家半導體產業的成功發展。這很大程度上歸結為文化。這歸結為公司創造的重點和紀律。這是勞動力,也是客戶群。
老實說,我認為在日本創建一家純粹的代工廠將非常困難。根據我所讀到的內容,臺積電不是在創建一個純粹的代工廠,而是一個客戶驅動/專用的設施。這是一家經過深思熟慮的混合合資企業。索尼需要更先進、更高性能的CMOS圖像傳感器來推動其不斷增長的市場。這種需求應該會推動臺積電的熊本工廠。
有很多,也許有 10-20 f臺積電的成功歸因于這些因素,包括技術突破、將研發從實驗室轉移到母廠的技能、更高的產量和專注的客戶參與等等。領先的客戶參與的例子包括 Apple、Nvidia、Qualcomm、AMD、TI、Sony、Fujitsu 等。 我在日本東京為德州儀器工作了 3.5 年,打過貿易戰,并與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談判——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制造和銷售半導體設備的截然不同的世界。
2005-2009年,當Rick Tsai擔任臺積電首席執行官時,我們在日本探索了不同的制造機會。富士通可能是最有前途的,因為它專注于先進技術,我們與他們探索了合資企業的方法。我們還探索了純晶圓代工模式,但日本政府阻止了這一模式。他們不希望臺積電在日本經營代工廠。為什么?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維方式、制造業遺產的包袱,以及日本政府高度民族主義的產業政策。
臺積電與索尼的做法是正確的:專注于一家或多家與當地客戶互動的合資企業。
問:疫情過后,日本政府的想法可能發生了變化。而現在,他們非常渴望讓半導體行業再次復蘇。臺積電宣布于2021年在熊本建造第一座晶圓廠后,進行了巨額投資,日本的許多晶圓廠今年開始量產。為什么臺積電在熊本晶圓廠成立合資企業,從小股東而不是全資子公司開始?
臺積電繼續做合資企業是非常聰明的。劉董事長和魏總明白,他們不必將100%的股本投入到投資中。他們可以通過技術、知識產權許可、其他合同、否決權等來維持控制權。他們可以巧妙地擴大產能,降低不會在財務上流血的風險。他們不必在他們不熟悉的外國做所有繁重的工作,就像在他們的祖國一樣。我們過去經常討論這個模型。盡管臺積電日本有很多非常了解日本文化的優秀人才,但任何一家外國公司,更不用說一家以華裔為基礎的公司,都很難在日本獨立取得成功。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是行不通的,我們在 TI 很清楚這一點。
問:是的。那么,為什么臺積電選擇在亞利桑那州獨自做這件事呢?他們應該選擇合資企業嗎?這會更有利于晶圓廠的發展嗎?
請允許我說,我不知道臺積電與聯邦和州政府或其任何客戶進行的任何討論的具體性質。但是,當我在那里時,鑒于創始人對WaferTech歷史的擔憂,我們總是談論在美國做一個獨立的代工廠。這次討論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一些人的嘴里留下了苦澀的味道,尤其是創始人的嘴里。您可能還記得,臺積電于 1996 年與三個合作伙伴在華盛頓州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但由于多種原因沒有成功。因此,臺積電迅速退出了該合資企業在WaferTech運營中創建獨立的代工廠。亞利桑那州計劃的起源是因為臺積電管理團隊的大多數成員在2005-2010年期間對何時何地在美國擴大生產進行了大量思考。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與IBM進行了多次談判,以收購其微電子部門,最后一次也是最認真的談判發生在2012-13年期間。這一切都是為了建立一個先進的實驗室,我們可以比合資企業更成功地控制和管理它。在我參與期間,亞利桑那州最初成為政治“建議”的地點,并受到大量補貼的誘惑。
問:你說日本政府很困難。然而,臺灣的半導體公司對美國政府的態度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對芯片彈性的重要性說了太多,卻無助于加快晶圓廠的建設和早期資金的分配。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包括臺積電在內的很多公司都認為他們可能誤解了地緣政治局勢。
華盛頓特區的動態有時變化很快,但大多數情況下,后續行動非常緩慢。與此同時,美國人的偏執導致了對最先進的工藝技術的不尋常關注,而不是同樣重要的遺留技術(不如最先進的技術)。華盛頓特區過分專注于推動臺積電建立其最先進的流程,并將巨額補貼與該流程節點聯系起來。而且,不幸的是,由于所有不同的機構都在爭奪有限的資金,而且 2024 年的選舉政治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資金已被大幅稀釋——到目前為止(也許它可能會改變)。我認為總共有 39 個州通過不同的技術中心獲得了一些 CHIPS 資金,這些資金可能過度稀釋了資金池。其中有多少會成功?我想說所有這些,但我不相信。
此外,對茶葉也有一些誤讀。很難說是誰的錯。我相信臺積電有一位強大而有能力的美國政府關系經理。聯發科也有個好人。這有點令人困惑,因為他們根據他們在“山上”與誰交談而得到不同的故事。請記住,CHIPS辦公室就像一家初創公司。盡管所有的官僚機構都在進行,但 CHIPS 辦公室沒有一年的時間。他們剛剛開始與日本經濟產業省、韓國的MOTIE、新加坡EDB等競爭。總會有一些溝通不暢。當太多的政客和游說者掌握這些重要資金時,就會變得令人困惑。必須不斷重新校準。你是對的,作為美國供應鏈一部分的重要和更大的公司需要得到比他們更好的待遇,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希望能夠進行重新調整,我們將在 2024 年 3 月的某個時候收到更積極的前景。
問:您是半導體行業為數不多的非技術專家之一,您在幫助國家和企業建立研發中心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您建議臺灣公司如何應對未來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謝謝你的贊美。不幸的是,一個人必須哭泣幾次塔爾球。日本也許是更難持續和成功地打交道的國家之一。新加坡稍微不那么復雜,盡管它的方式非常官僚。無論是在日本、新加坡還是韓國,本地團隊都必須在本地和“外國”管理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在日本,只有日本管理層的外國公司無法踏入日本政府組織的大門。有時,需要更自信的美國或歐洲管理層。
例如,當我在TI工作時,Jerry Jenkins(當時的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采納了我的建議,派我和另外兩名美國經理住在日本,協助貿易和商業談判。我們最終成功地打開了市場,談判了貿易協定和合資企業,并在我離開 TI 時將 TI 在日本的銷售額從大約 2 億美元增加到 16 億美元。
我花了很多時間成功地處理日本政府的關系,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后來成為警察廳的副部長,并與我一起工作了多年。跟隨我的諾姆·諾伊特(Norm Neureiter)也非常成功。沒有人會進入政府的內部圣殿。然而,有效的溝通是必不可少的,擁有一支強大的政府關系團隊 24/7 全天候工作至關重要。
有了索尼作為核心合作伙伴,臺積電做對了。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富士通和瑞薩電子也是很好的潛在合作伙伴。公司必須有全職的政府關系和員工來管理它,理解它,并支持國家經理和晶圓廠經理。多元文化的存在也是在日本和亞利桑那州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對于臺積電,我曾向張董事長和臺積電的其他高級管理層建議,我們應該將里克·卡西迪(Rick Cassidy)從美國派往日本——當時我們第一次考慮在日本制造。取而代之的是,派出了一位實力雄厚的臺灣經理,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我們不應否認,文化競爭/分歧需要更有經驗的外國顧問加入當地團隊。無論如何,成功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與政府機構的持續溝通——讓他們覺得他們是了解您的目標和目的的企業的一部分,并且永遠不會讓他們感到尷尬。
審核編輯:黃飛
-
臺積電
+關注
關注
44文章
5632瀏覽量
166407 -
晶圓
+關注
關注
52文章
4890瀏覽量
127931
發布評論請先 登錄
相關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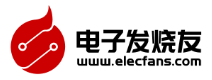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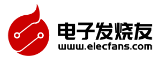


 談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和日本的發展策略
談臺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和日本的發展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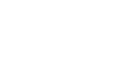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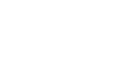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