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駕駛第一案”——從谷歌3月初起訴Uber侵犯其自動駕駛知識產權已經持續近一個月。該案直到4月上旬才會宣判,而面對谷歌的步步緊逼,Uber方面至今也未給出一個反轉性的回應。雖然該案這個月才爆出,但其背后,是谷歌Uber在地圖、出行行業積怨已久,如今終于迎來了一個爆發點。
從五年前谷歌投資Uber 2.58億美元,到今天的對簿公堂,雙方到底發生了哪些恩怨情仇?復盤兩家公司相愛相殺的五年歷史,可以看到從投資合作到業務互搏、挖高層墻腳以至不擇手段奪取自動駕駛技術的商業暗戰。
200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輟學生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創辦了一個租車應用,Ubercap。頭腦靈活的卡蘭尼克干的是四兩撥千斤的活——承包當地市場的閑置用車,再轉租出去。后來他發現閑置的司機其實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資源,于是后來的事我們都知道,Uber誕生了。
同年的谷歌在大多數人印象中還是一個搜索引擎,對它發布的Android2.0都知之甚少,更不要說谷歌Google X那些隱秘的黑科技。但兩年前從斯坦福大學請來的塞巴斯蒂安特龍創辦了無人駕駛項目,一向以技術超前聞名的谷歌,悄悄地從基礎而又尖端的控制系統,切入汽車領域,準備來個底朝天的顛覆。
兩個公司都在接下來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中氣勢如虹,但新興的Uber發展速度更甚一籌,力壓競爭對手sidecar,以及另一家Lyft,公司業務火箭式上升。
一、價值2.58億美元的短暫蜜月
2013年,高速擴張的Uber謀求新一輪融資,此前“錯投”Sidecar的谷歌當然不會放棄這一明日之星。谷歌風投提前和卡蘭尼克聯系上,要趕在其他投資人之前搶到Uber稀缺的份額。面對Uber開出的高價,谷歌并未猶豫太久,最終給出了2.58億美元的投資。有趣的是,在那時,卡蘭尼克就顯出了面對巨頭絲毫不懼的氣質:都說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但對給出了如此大份額的投資金主,Uber一開始壓根連董事席位都沒想給人留。經過幾輪談判,Uber才松了口,讓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法務官大衛·德拉蒙德進入Uber董事席。
不過摩擦歸摩擦,這樁生意還是讓雙方都受益良多。谷歌風投付出2.58億美元,日后估值達到了35億美金,回報率近14倍;Uber則拿到了高速擴張急需的資金,又滿世界地開疆拓土去了。并且,Uber提供的出行業務和谷歌地圖高度相關,這一聯手可以說是天作之合。基于此,盡管這一結合在內里有不可言說的分歧,表面上顯露的更多是雙方甜言蜜語,你儂我儂,你耕田來我織布,攜手共建新生活的美好圖景。也正是看到兩者在業務上的相關性和資源的互補性,外界紛紛喧囂,谷歌必將收購Uber,把地圖和打車整合。
但谷歌保持了克制,一方面這樣做的風險太大;另一方面,世人那時還不了解卡蘭尼克的“狼子野心”——這個“敢于和政府對抗(卡蘭尼克此前創業時,為保證公司的運營而不給員工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狂人,根本不甘于寄人籬下。早年創業經歷困難時,卡蘭尼克睡公司、睡租來的車上,在賭場廁所里洗澡,還不給自己發工資。度過了所有這些苦痛而孵化出來的Uber,是卡蘭尼克苦難與夢想的結合,是他的心頭肉,怎會輕易割出。無懼巨頭的底氣來自于卡蘭尼克堅決的信念——Uber就是下一個巨頭。
Uber 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
今日Uber估值近七百億美元,很大程度要歸功于卡蘭尼克毫不動搖的信念以及圍繞這一信念堅定邁出的擴張步伐。然而Uber近來困頓的源頭可以說也是卡蘭尼克——由他一手建立的侵略性的企業文化讓Uber四處樹敵,把政府、企業、普通民眾得罪了個遍,在Uber內部也形成了一種弱肉強食的生態。這種侵略性,也在日后為谷歌與Uber的恩斷義絕埋下了伏筆。
二、愛上一匹野馬 可我的家里沒有草原
卡蘭尼克在Uber和谷歌建立關系后,立即就開始著手向谷歌要資源。除了利用谷歌地圖做導航支持,卡蘭尼克還要求在谷歌地圖APP中接入Uber的打車服務。谷歌隨后答應了這個要求,Uber卻不開心了。因為谷歌這個接入的時間,給得太晚,“拖慢了Uber利用谷歌入口進行快速擴張的步伐。”
而除了在反應速度上跟不上Uber的要求,谷歌地圖在某些地區無法提供服務(比如中國)也讓卡拉尼克大為光火。傻子都知道地圖對一款打車軟件是何等重要,面對中國這樣體量龐大的潛在市場,最關鍵的地圖服務谷歌卻給不了。為了快速切入中國市場,Uber在2014年年底與百度達成合作,接受百度戰略投資,同時由百度提供地圖服務和百度地圖APP內接入。(當然,對于長袖善舞的卡蘭尼克來說,合作伙伴肯定是多多益善,因此高德也是合作商之一)對于谷歌來說,這著實有些尷尬——作為一個當大哥的,當初吸引Uber這個小弟拜入門下的基礎性資源現在卻沒法提供,逼得小弟和競爭對手談合作。但谷歌只能悶聲吃大虧,誰叫當初退出了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谷歌任由Uber與競爭對手合作是無奈之舉,不得不放手。然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谷歌真正體驗了一把被背叛的滋味。2015年3月,Uber宣布收購地圖初創企業DeCarte,發言人稱“將繼續改善基于地圖的產品和服務”。話說得很婉轉,但聽在谷歌耳朵里分明就是“大哥,小弟我翅膀長硬了,自立門戶去了。”這一天,谷歌風投主導投資Uber的馬里斯和克萊恩一定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就是活生生的現代企業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
不過從Uber的角度看,這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隨著體量的不斷膨脹,Uber產生著越來越多人們出行的相關數據,這些數據蘊含著極大的潛在價值——它不僅指示著城市中的交通流量,為更智慧的交通調度提供分析基礎;還指出了人們的活動范圍和目的地,這對適時挖掘人們需求,提供精準的本地服務有著非常大的意義。在Uber將業務逐漸擴展至打車以外的本地服務上時,無論是對于卡蘭尼克個人的巨大野心還是對于Uber的未來發展,委身于谷歌都不再合適,擁有自己的地圖此時顯得愈發重要。
2015年6月,Uber又將微軟Bing地圖業務收入囊中。Bing提供的完整數據意味著Uber在地圖上真正不再完全受制于谷歌。與數據一同來到Uber的,還有約100名微軟的圖像技術工程師,連同之前收購的DeCarte,Uber的地圖團隊人數超過150人。對任何地圖公司來說,這樣一支隊伍都是不可小覷的。同年11月,放棄收購高精地圖廠商Here的Uber又開始了拉幫結派的活動,和荷蘭導航廠商TomTom達成合作,拿到了后者提供的全球300多座城市的數字地圖和交通數據。
更讓谷歌郁悶的是,Uber還接連兩次,分別于2015年6月和12月挖走了谷歌地圖業務主管布萊恩·麥克蘭登(Brian McClendon)、地圖產品管理總監馬尼克?古普塔(Manik Gupta)。
布萊恩·麥克蘭登(Brian McClendon)
谷歌此時對Uber的情感可謂十分復雜。一方面,Uber擴張得越厲害,谷歌那2.58億美元的投資回報就越高;另一方面,這些回報的代價卻是Uber一點點蠶食谷歌在地圖上的統治力。谷歌最初的設想是以地圖“圈住”Uber,在分工合作中實現價值。然而Uber豈是凡物,這匹志在千里的野馬可受不了束縛,如果你不能為它提供一片草原,那就要做好準備被啃光家中的草坪。不過對于谷歌來說,這片草坪可是會結出金子來的寶地,相對于投資Uber獲得的回報,自家地圖延伸開來的數據挖掘和本地市場服務的想象空間顯然更加廣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面對主動發起挑戰殺進自己重要領域的Uber,谷歌發動了反擊。
三、谷歌Waze的回擊:一顆提前落下的子
要說谷歌是一朵純潔的白蓮花,在這場恩怨中有多么無辜,那也不見得。在商界摸爬滾打多年的谷歌,對如何規避風險自然是了然于心。可以說,投資Uber本身就是谷歌涉足共享出行領域的一個對沖措施(谷歌此前已經投過Uber的競爭對手sidecar)。兩頭下注不夠的話,還可以再來一家。2015年初,谷歌的語音助手服務Google Now(該項目現在已被邊緣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谷歌新語音助手Google Assistant的前身)接入美國第二大打車平臺Lyft。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間點是早于谷歌收購DeCarte的。也就是說,盡管雙方很可能早就知道彼此“心懷鬼胎”,但在實際的“使絆”動作上,是谷歌跨出了第一步。
奈何Lyft不給力,完全沒有給Uber造成足夠的威脅。這種情況下,谷歌只能親自上了。2016年8月底,谷歌正式通過旗下的眾包地圖應用Waze在舊金山地區推出了共乘出行服務,在Uber的老巢與其抗衡。要說到這個Waze,那就不得不感慨姜還是老的辣,這顆棋谷歌早在2013年就埋下。
幾乎是在投資Uber的同時,谷歌斥資9.66億美元從蘋果和Facebook的包圍中收購了以色列眾包地圖及導航軟件Waze。不過就當時來看,谷歌并沒有立馬將推出出行服務提上Waze的日程。收購Waze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Waze的眾包模式,優化谷歌對即時交通信息的更新以及對更精準地圖信息的需求。同時,Waze上的社區聚合了一批活躍的用戶,他們在其中制造、分享著關于本地信息的大量內容,也相互建立著關系,對于谷歌一直想要找辦法切入的社交,這是一個不錯的渠道。
Waze之所以廣受歡迎 很可能是logo因為長得萌
鑒于共享出行本質上也是連接人和人,Waze的這一社交屬性讓它可以非常平滑地推出共享出行服務。在2015年7月,也就是Uber收購微軟bing地圖業務后,谷歌首先讓在Waze在以色列試點了拼車軟件RideWith,用這一舉動向決意出走的小弟隔空示了個威。要說谷歌也真沉得住氣,每天就只讓司機接兩單(某種意義上這才是真正的共享出行,司機都是兼職而非專職,主要接順路乘客,上班一單下班一單)。這一試點就試到了2016年5月,近一年后,谷歌終于讓Waze的共乘服務走出以色列,登錄美國,在谷歌的硅谷總部及周邊地區,開啟了,呃,新一輪試點。當時間終于來到上述的2016年8月,谷歌才在舊金山全面鋪開了Waze的共乘服務。
從谷歌的動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媒體對谷歌Waze與Uber的競爭實際上有一些誤讀。在出行服務上,兩者其實處在一種不完全競爭的關系:Uber有眾多專職司機,提供按需出行,掙車費做工資;而谷歌的Waze所有司機均為兼職,主要載人坐個順風車,54美分一公里的價格只能補貼油費。
面對此時估值已沖破500億美元的Uber,谷歌選擇避其鋒芒,小角度切入,其實也并未對Uber造成太大影響。真正讓Uber如鯁在喉的,是Waze的眾包模式和強社交屬性。打車服務只是Uber的第一步,到現在都仍未實現盈利(2016年上半年虧損12億美元),要更深層次地掘金,還得靠基于汽車平臺的數據挖掘和本地生活服務生態。在這兩個方面,背靠谷歌的Waze一點不比Uber弱,甚至因為Waze上社區的存在,依靠人際關系的影響力,它在本地生活服務上比Uber的滲透性更強。今年2月,谷歌宣布Waze的共乘服務將向全美拓展,聽聞這一消息的Uber高管們,想必不會泰然自若。
谷歌與Uber緣起地圖與出行,卻又因地圖及出行和Uber分手。戀人們總是因為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而在一起,最終又因為實際相處中的利益糾葛而中斷關系。對于谷歌和Uber來說亦然,商業利益的劇烈沖突下,雙方的伙伴關系走向破裂,只是時間問題。
四、自動駕駛無間道
行文至此,谷歌與Uber在“前自動駕駛時代”的恩怨可以說基本厘清。對于大公司來說,合作、制衡、背離都是相當正常的情況。在商戰中,這些故事并非新鮮橋段。對于谷歌和Uber來說,雙方雖然各自殺入對方的領域,但是并未對對方的統治力構成威脅,因此也無需撕破臉皮。
但隨著新趨勢的到來,一場更大的矛盾在等待著雙方。在2013年深度學習迎來爆發后,自動駕駛被越來越多地提上了日程。對于谷歌和Uber來說,自動駕駛都是寸土不讓的技術高地——谷歌在這一領域具有先發優勢,已積累數年,盼望著在未來攜自動駕駛技術橫切整個產值巨大的汽車行業與出行市場;而Uber則可以憑借無人駕駛將所有司機送回老家,不僅省下人力成本,還能極大地提升平臺汽車的利用率,抬高整個打車平臺的利潤率,更進一步,它也可以像谷歌一樣成為技術供應商,賺取不菲利潤。自動駕駛的誘人紅利,讓雙方的競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谷歌方面起步早,09年自動駕駛由塞巴斯蒂安·特龍立項,至今已有8年。但是谷歌的心氣太高,非完全自動駕駛不做(L4及以上),但是實現難度又太大,遲遲無法落地。在未能商業化的這么多年里,谷歌的無人駕駛測試車從雷克薩斯Rx450h換到了谷歌自家的Self-driving再到菲亞特克萊斯勒的Pacifica,項目主管從斯坦福來的塞巴斯蒂安換成了卡耐基梅隆來的厄姆森再到福特來的克拉福克西,包括核心高級工程師安東尼·萊萬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內的一批頂尖技術人員也流失不少。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谷歌還是憑借先發積累在路測里程和系統可靠性上占據優勢。
谷歌三代自動駕駛測試車的變遷
Uber方面至2015年才起步,但舍得花血本,一立項就買下了自動駕駛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學機器人研究所的五十多名研究人員。馬不停蹄地,Uber改裝了福特Fusion做測試車,隨后又在2016年8月拉來沃爾沃,用上了后者的SUV XC90。在路測方面,Uber先是在加州與匹茲堡兩地同時測試自動駕駛,后來因為自動駕駛車闖紅燈被逐出加州(這個月剛剛通過申請測試許可重返加州),轉而到亞利桑那開辟新的陣地(這周Uber的XC90測試車出事的地點temple市,就位于亞利桑那)。同時,Uber的激進風格也注入了無人駕駛項目,在亞利桑那和匹茲堡,Uber都推出了面向乘客的自動駕駛服務,不過車上仍配有司機。
圖為Uber自動駕駛測試車沃爾沃 XC90
單看以上背景,谷歌和Uber在自動駕駛的競賽仍然處于隔空喊話的狀態。但2016年8月的一項收購,讓兩者有了實質性的矛盾,而且這矛盾不來則已,一來驚人:Uber在該月斥資6.8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卡車自動駕駛公司Otto。而后者才由當年1月從谷歌自動駕駛項目離職的安東尼·萊萬多斯基建立不久。萊萬多斯基進入Uber后,立即被委以重任,成為其自動駕駛項目的主要負責人。
卡蘭尼克與萊萬多斯基(右)
雖然中途萊萬多斯基創辦了一個自動駕駛公司,但對谷歌來說,這種感覺再熟悉不過了:這貨又來挖我的人!對于至關重要的自動駕駛技術,谷歌自然不能再對Uber挖墻腳的行為聽之任之。對得力干將轉投他人一事,谷歌保持沉默如此之久,想必是在暗中搜集證據,那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本月初,已經改名Waymo并成立公司的谷歌無人駕駛投下一顆重磅炸彈,起訴Uber通過萊萬多斯基盜竊了谷歌的激光雷達技術,要求后者立即停止對其技術的侵權使用。對自動駕駛較為熟悉的讀者應該知道,激光雷達是現今自動駕駛業內的核心硬件設備,在自動駕駛車輛構建高精地圖、對周圍環境進行感知從而引導車輛自動駕駛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面對Waymo的指控,Uber稱這只是為了拖慢其自動駕駛腳步的手段。然而Waymo給出了更為詳盡的證據鏈:
在Waymo員工Pier-Yvez Droz的證詞中,萊萬多斯基曾于2015年私下會見了已經被Uber挖走的前谷歌地圖業務主管布萊恩·麥克蘭登(Brian McClendon),萊萬多斯基還向該員工透露了他離職創辦新公司的意愿,以及Uber有意購買谷歌激光雷達研發團隊的消息。
Waymo聲稱2015年12月,萊萬從谷歌儲存自動駕駛資料的電腦中下載了大量敏感文件(一萬四千多份)和數據,而后者面對指控承認了這一點,但他解釋稱只是為了方便在家辦公。
2016年2月,萊萬多斯基離職后一個月,新公司Otto宣告成立。同一個月,萊萬被卡蘭尼克聘請為自動駕駛顧問。
2016年5月,Otto開始“隱身”,同月,Uber傳出了開始進行自動駕駛測試的消息。
2016年8月,Uber正式收購了Otto。(另外,那個文章開頭提到的,谷歌費盡千辛萬苦才送入Uber董事會的Alphabet首席法務官大衛·德拉蒙德,也在這個月從Uber董事會離職,原因是兩家公司在自動駕駛領域存在潛在的巨大沖突。)
如果以上種種都可以說是谷歌的一面之詞的話,那么有一個問題對于Uber來說非常致命:如果真如萊萬多斯基所說,他們的激光雷達系統是收購了傳感器廠商Tyto后自行研發,那為何與Waymo的設計高度相似?
對于Uber來說,現在的情況十分不利。首先是Uber整個公司因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而陷入輿論的風口浪尖,多名高管相繼離職;緊接著上周末Uber的自動駕駛XC90測試車在亞利桑那Temple發生車禍,雖然警方確認不是Uber方面的責任,但公司還是緊急叫停了自動駕駛測試。而對于來自Waymo的指控,雖然審判結果要到4月上旬才宣布,但此事仍在持續發酵,一旦Uber無法洗脫其罪名,被扣上盜竊知識產權的帽子,無論是在自動駕駛技術的使用還是在公關形象上,Uber都將面臨新一輪打擊。遺憾的是,直到現在,Uber仍未提出能夠證明其清白的關鍵證據。
不過,一切尚未蓋棺定論,這場迷霧重重的“自動駕駛第一案”,尚有許多疑點需要揭開。雖然這場堪比無間道的商戰又給吃瓜群眾奉獻了一場大戲,但對于當事雙方來說,似乎都沒撈到好處。谷歌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核心力量,要知道,谷歌自動駕駛項目的創立基礎之一,正是萊萬多斯基研發的501系統。另一方Uber現在則面臨著嚴峻指控,隨時可能在公司眾多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
結語
回望谷歌Uber這場長達五年的恩怨情仇,不知當事雙方是否會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見。Uber從創業起步到估值數百億美元,然后開始和當年提攜過的大佬正面開戰,故事的精彩程度不亞于一部黑幫電影。故事接下來會怎么講?是新玩家干掉老派大佬,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被老大哥壓制住?后面的官司會給出分曉。
做一個架空的假設,如果當初谷歌和Uber能求同存異,競爭中謀合作,谷歌發揮技術優勢,Uber發揮車輛平臺優勢,兩者是否能提前做大并分得自動駕駛這一枚大蛋糕呢?只是哪有那么多如果,技術趨勢常常是難以預見的,而競爭的結果也一樣。反過來,或許這一案也不完全是壞事,但愿后來的玩家能從中汲取經驗,多一些正常的競爭與合作,不再將自動駕駛的競賽玩成“負和游戲”。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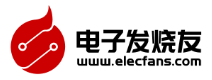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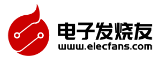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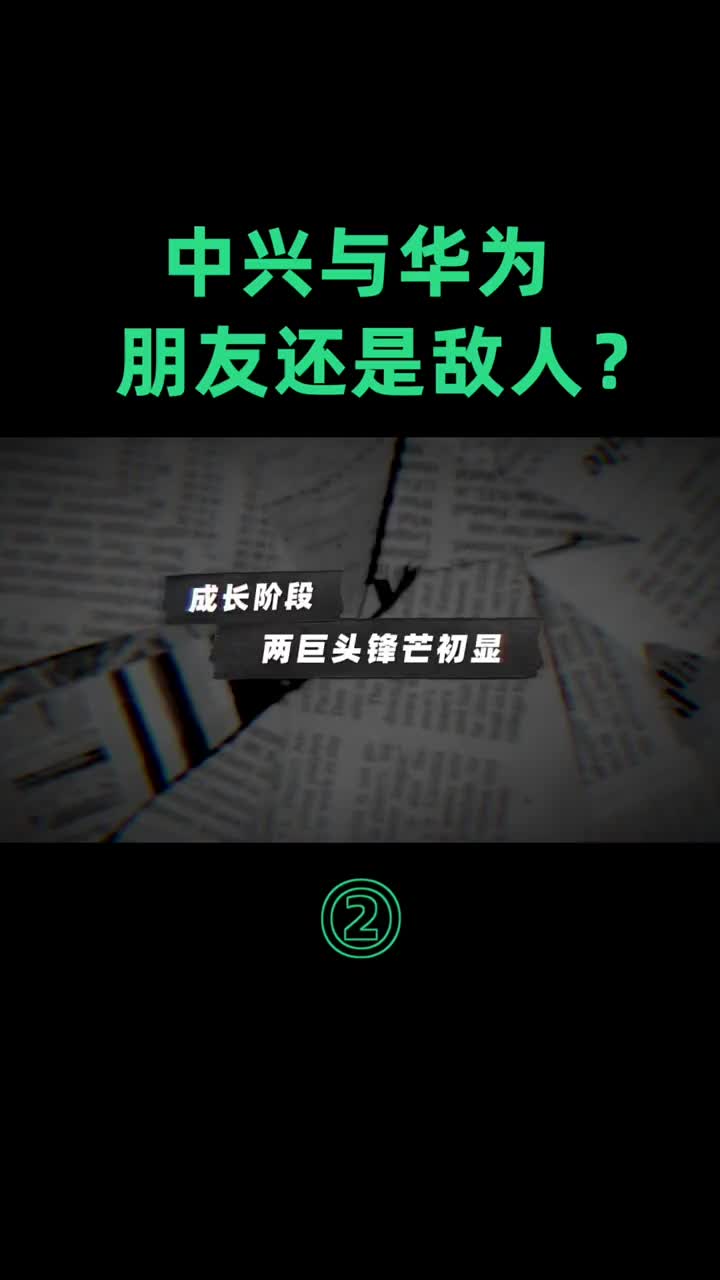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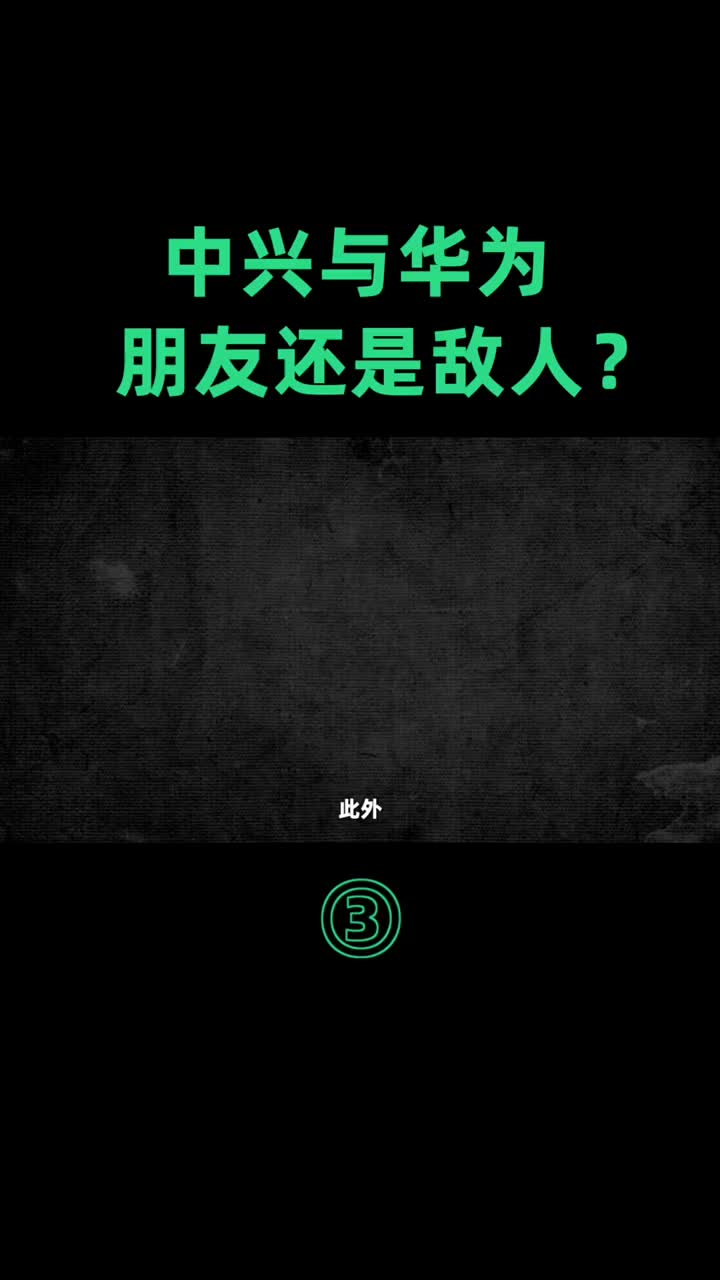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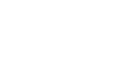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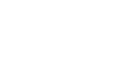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