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車企江淮汽車(下稱“江淮”)或將面臨重大處罰,三天后在北京舉行的一場聽證會將起到關鍵作用。
5月9日晚,這家老牌車企就“涉嫌排放造假”發布澄清公告,并公告了聽證日期。
但對現年62歲的江淮董事長安進而言, 他屆時或許無暇顧及。在他案前,一張近九年來最差的業績成績單,足以讓他焦頭爛額。
去年,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國資車企財務數據全線惡化:凈利潤同比下降282.02%,虧損7.86億元;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34.54億,資產負債率則高達71.10%。
安進曾將翻身大計寄望于新能源汽車產業,力促與德國汽車巨頭大眾成立合資公司。但這項合作被疑生變,合資大戲或許正悄然演變成“獨角戲”。
半個月前,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公布的《環境影響報告書征求意見》顯示,大眾并未出現在該工廠建設環節,其建設注資主體僅為江淮一家。
如今,新能源汽車市場的“混戰”正踏步進入下半場。在新的游戲規則下,這家成立55年的老牌國企命運變得愈加迷茫。
腹背受敵之時,安進能否帶領江淮沖破體制的藩籬,在民企與外企的雙重夾擊下實現突圍?
大眾“棄子”?
一周前,身處安徽合肥的安進收到一份來自北京的聽證通知。北京市生態環境局去年的一次產品抽查,讓江淮處境尷尬。
由于發現江淮涉嫌對污染控制裝置以次充好、冒充排放檢驗合格產品出廠銷售,抽查部門擬對其進行重大處罰舉行聽證。
當收到因質量問題接受處罰聽證的通知時,安進或許會想起三年前與大眾在質量控制等方面商議合作的場景。
當年,安進與大眾汽車集團(中國)原總裁兼CEO海茲曼簽訂諒解備忘錄。
9個月后,在中德總理的雙雙見證下,大眾和江淮在柏林正式簽訂合資協議。根據協議,雙方各斥資10億元,建立合資公司,股比限制在50:50。
按照原計劃,合資企業將投資50.6億元,在合肥建設年產能為10萬輛電動車的新能源工廠。
彼時,這位中國汽車界的領軍人物出席公開場合時常滿面笑容。這個合資項目,讓他看到借力大眾,實現在新能源汽車領域跨越式發展的可能。
協議規定,大眾應幫助合資公司對大眾特定的PQ平臺進行電動化改造,在設計開發、試驗驗證、產品制造、質量控制和供應鏈開發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
但安進的如意算盤很快遭遇大眾的冷漠,并逐漸落空。從合資公司成立至今,海茲曼和現任大眾(中國)管理董事會主席迪斯,均未兌現諾言。
大眾的冷漠折射出商業世界的冷血殘酷。
事實上,大眾當初選擇與江淮合作,一定程度是出于應對中國雙積分政策的考慮。
雙積分政策是中國政府為平衡新能源汽車與燃油車發展而出臺的一項強制規定。
這項政策以2018至2020年為限,對純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汽車等新能源汽車作出相應的積分規定,車企想要出售燃油車,就需要同等量的新能源汽車積分來抵消,多余的新能源汽車積分可用于交易。
彼時,中國相關法律還不允許外資車企在華獨資建廠。
雙積分政策下,大眾不得不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尋找本土合作伙伴。在與江淮的合作中,大眾明確將“新能源積分第一購買權”寫入合同。
但江淮并非大眾的唯一選擇。隨著上汽大眾安亭工廠落地,江淮的地位開始變得尷尬。
去年10月,這座大眾集團全球首個采用MEB電動化平臺建設的汽車工廠正式開工建設。該項目總投資170億元,計劃于2020年全面投產,年產能達30萬輛。
開工現場,上汽集團董事長陳虹聲稱,未來安亭新能源工廠將生產大眾集團近乎所有新能源汽車。
就在上汽大眾工廠奠基的同時,一汽大眾銷售有限責任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孫惠斌透露,該公司也將在2019年投放三款大眾品牌新能源車型。
此外,海茲曼還曾引入滴滴,成立合資公司,計劃組建共享出行車隊。車隊將使用六萬輛大眾品牌的新能源汽車。
安進不惜動用高層資源開啟的這場豪賭,如今正隨著雙方力量對比失衡而顯得希望渺茫。
“江淮汽車對自己的認識越來越清醒。”他說。
但安進并不甘于“棄子”的命運。面對資金壓力,他依然選擇豪賭50億,獨家注資合資公司的新能源工廠。
這位效力江淮44年的老將不得不重回自力更生的老路。原計劃的“大眾技術”仿佛海市蜃樓。江淮大眾如今擬投產的三款車型,似乎僅有江淮孤影。
長期以來,江淮面臨著關于其新能源汽車“產品力并不出眾”的質疑。
如今,大眾的疏離,使身處困局中的安進顯得愈發捉襟見肘。
風暴將至
半個月前,一份足以令人焦慮的財報擺在安進案前。
進入2019年,江淮的危機并未好轉。一季報顯示,拿到國家補貼后,該公司凈利潤仍僅剩6464萬元,同比下滑近70%。
在這場持續數年的危機中,安進曾試圖力挽狂瀾。一年前,江淮交出2017年成績單,凈利潤同比下滑62.83%。
這份八年最差凈利,迫使安進做出姿態。他效仿長城董事長魏建軍和總裁王鳳英自罰300萬和200萬年薪的做法,用高層薪酬減半,來表明重回自主品牌主流隊伍的決心。
這并非江淮第一次面臨危局。早在三十年前,這家位于巢湖之濱的地方國企就曾深陷危機。
1990年,安進的前任左延安執掌江淮,開始推行改革。
這位“江淮教父”斷臂求生,放棄整車,專注底盤,終于實現突圍,連續三年位居行業第一。
實現造血后,左延安帶領江淮重回整車界。短短幾年,其輕卡業務就躍居全國第二。
此后,江淮乘勝追擊,從一家默默無聞的地方小廠,躋身中國汽車工業八強。
安進或許對那場翻身仗中的眾志成城記憶猶新。此時,他寄望于通過自罰措施,鼓舞士氣,重振輝煌,但收效甚微。
次年,江淮創下虧損7.86億元的新紀錄。
如果沒有國家補貼的遮羞布,這份紀錄將更加難看。
據「角馬能源」統計,2014年至2018年五年間,江淮的凈利潤合計21.95億元。但這五年間,該公司合計收到各類政府補貼高達87.18億元,其實際虧損超過65億元。
其中,僅2018年江淮就至少拿到6輪政府補助,總金額約為11.06億元。這意味著其2018年實際虧損已接近20億元。
這家依靠國家補貼生存的新能源車企在政策劇變風暴中難以為繼。與去年相比,今年補貼標準平均退坡超過50%。補貼退出已成定局。
“江淮新能源汽車的興旺和國家政策補貼有著直接關系,但隨著政策退坡,其將面臨巨大挑戰。如果在資金和產品力方面跟不上,或將難以為繼。”汽車行業分析師鐘師說。
補貼退坡后,江淮多年來的多元化打法惡果初現。
這家曾經以專注著稱的車企,如今已把版圖擴張到商用車、乘用車、客車、零部件和汽車服務五大業務板塊。
但瘋狂擴張的背后,是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現實。
安進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江淮全力推行商乘并舉戰略下,其乘用車并無拳頭產品。商用車試圖向乘用車轉型,也困難重重。
這位年過花甲的掌舵者面臨著比過去數十年更為復雜的競爭形勢。
在國家政策大力扶植下,造車新勢力迅速崛起。李想、李斌、何小鵬等明星創業者開始嶄露頭角,許家印、董明珠等大佬也紛紛加入戰局。
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兵戈搶攘之時,外企早已虎視眈眈。
去年4月,國家發改委取消新能源汽車整車制造的外資股比限制。
九個月后,在距離上海市中心73公里的臨港產業園,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決定砸下500億元重資,在面積達86萬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設一座產能達50萬輛純電動汽車的超級工廠。
這座特斯拉在美國本土之外的首個超級工廠,宣告外資車企由此進入在華獨資建廠時代。
大眾也得以擺脫合資的掣肘。政策變局下,其與江淮的合作前景撲朔迷離。
“越來越清醒”的安進,依然選擇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孤注一擲。他希望復制前任左延安起死回生的故事。
但左延安的終極困局至今未解。這位在汽車行業率先提出“混改”的國企干將,曾深受體制之苦。
在競爭慘烈的汽車市場,這或許才是制約國企與民企競爭的最大障礙。
在補貼退潮引發的淘汰賽風暴中,安進掌舵的這艘已有55年歷史的大船,將何去何從?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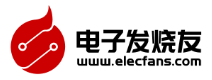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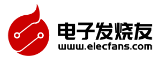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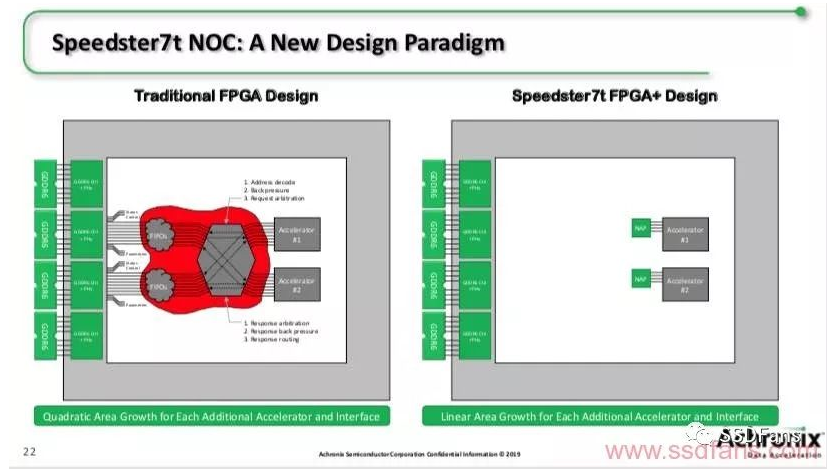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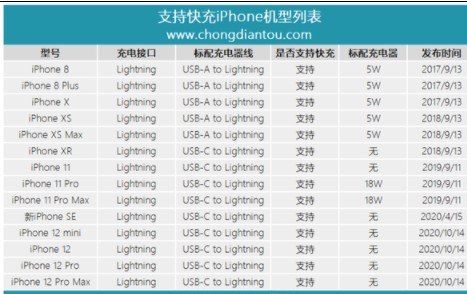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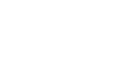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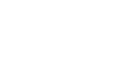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