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蘭德哲學家認為人工智能跟煉金術一樣不可能
“改變人們觀念需要的不僅是才華,還有勇氣”。
摘要:1965年12月,休伯特·德雷大眾以蘭德公司顧問的身份,發表了編號為P-3244的《人工智能與煉金術》的研究報告,對蘭德公司本身主導的人工智能(以下簡稱AI)研究提出了重大理論挑戰,1972年德雷大眾以該報告為基礎出版了《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該書與1966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ALPAC報告,1973年英國科學研究理事會的LightHill報告一起,標志著AI發展歷史上的第一次冬天,即使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由于專家系統興起的AI再次繁榮,以及90年代初AI的第二次冬天,AI的研究綱領已經變化甚多,但德雷大眾仍然堅持其基本觀點,對隱含在AI研究綱領中的關于人類認知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深層假設,從現象學和海德格爾哲學為核心的大陸哲學立場出發,始終進行批判性地思考和分析,無論AI科學家共同體對其觀點是否認同,德雷大眾這些深刻的哲學思考,客觀上推動了從AI研究早期基于知識主義、符號主義強綱領的盲目樂觀,到目前對實現人類級別智能的智能機器建造的審慎態度,以及更加豐富的研究進路的轉變。
關鍵詞:德雷大眾,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冬天
一、德雷大眾生平及學術工作概述
休伯特·德雷大眾(HubertDreyfus),1929年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的特雷霍特(Terre Haute),在哈佛大學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64年在奎因的學生Dagfinn F?llesdal指導下,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者來自挪威,主要研究語言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和解釋學1。
作為美國知名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家,德雷大眾是歐洲大陸哲學的主要代表:胡塞爾、福柯、梅洛-龐蒂,尤其是海德格爾在美國頂尖的譯者和詮釋者,他的《在世存在:海德格爾 述評》第一部,被許多人認為是本科生學習海德格爾最重要的哲學思想的權威讀本,他與Paul Rainbow合著了《米歇爾·福柯:超越結構主義和解釋學》,還翻譯了梅洛龐蒂的《意義與無意義》,但他最為人所知的工作是其從哲學角度對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的思考和批判,代表作主要是1972年的《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以及相關論文,1982年他與Harrison Hall合編的《胡塞爾、意向性與認知科學》也是研究胡塞爾現象學與認知科學關系的經典論文選集2。
1968年以后德雷大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了他主要的學術生涯,之前他先后任教于布蘭迪斯大學(1957-1959),麻省理工學院(1960-1968),1998年荷蘭伊拉姆斯大學因其“在人工智能領域杰出和有高度影響力的工作,以及對20世紀大陸哲學的分析和詮釋所做的同樣杰出的貢獻”而授予其名譽博士,2001年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3。
德雷大眾桃李滿天下,既包括提出了GOFAI(Good Old 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概念的John Haugeland(1945-2010),還包括哈佛大學哲學系主任Dorrance Kelly,以及Taylor Carman、Iain Thomson、Mark Wrathall這些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中年哲學家,2010年音樂家和導演TaoRuspoli在德雷大眾的影響和指導下,拍攝了反映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紀錄片《在世存在》,采訪了美國主要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其中除德雷大眾本人之外,約一半學者均為其學生4。
二、蘭德報告《煉金術與人工智能》的主要內容
1964年夏天,麻省理工學院的年輕教師休伯特·德雷大眾由其弟弟斯圖亞特·德雷福推薦,進入蘭德公司圣塔莫尼卡總部擔任研究顧問,公司當時負責計算機科學部門的主管Paul Armer認為AI研究需要考慮哲學問題并能從中獲益,而德雷大眾的簡歷和背景調查都不錯,讓他覺得德雷大眾可以為AI研究項目從哲學上提供公正的建議[1]。
蘭德公司在早期AI歷史上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當時其研究經費主要來自于美國空軍等軍方機構,對通用數字計算機的建造和研究情有獨鐘,不僅聘請馮·諾依曼擔任顧問,還委托普林斯頓大學建造了JOHNNIAC,最早的程序存儲結構(馮·諾依曼)數字計算機之一。50年代他們聘請了Allen Newell從事北美防空指揮系統自動化的研究,Cliff Shaw為JOHNNIC上提供了最早的交互式解釋型編程語言之一JOSS,Newell、Shaw與公司顧問,卡內基理工學院教師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及其部分學生一起,在推動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1963年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院任教的Feigenbaum和Feldman選編了AI當時最重要的論文文集《計算機與思維》,書中收錄的20篇論文中有6篇是蘭德的研究報告[2]。
Paul Armer沒有想到的是,德雷大眾提交的報告是如此尖銳,幾乎摧毀了蘭德正在進行中的AI研究的基礎,他不得不延遲公布該報告,直至他認識到“僅僅是因為不喜歡不能成為不出版它的理由”,最終推遲了大約9個月于1965年12月出版,該報告后來成為蘭德公司銷量最高的報告之一[3]。
德雷大眾的報告標題是《煉金術與AI》,將AI與歷史上的煉金術相提并論,意圖說明當時進行的AI研究是沒有基礎的無用之功,而且在序言中,他針對Feigenbaum和Feldman在《計算機與思維》中所宣稱的AI領域的顯著進步是向終極目標的逐步接近的說法,提出了第二個尖酸的比喻:第一個爬上樹的人可以聲稱這是飛往月球的顯著進步[4]。
這份編號為P-3244的蘭德公司報告當然不僅是因為標題和序言的激烈比喻而影響重大,關鍵還是報告中的觀點確實對早期AI發展的成就提出了重大挑戰。
報告共90頁,分為以下四個部分[4]:
(1)序言
(2)Part I:人工智能領域的現狀
(3)Part II:當前困難的潛在意義
(4)Part III:人工智能的未來
報告共引用了43篇文獻,其中13篇來源于早期AI的核心文集《計算機與思維》中的論文,8篇來自于AI方面及其相關的專業期刊,8篇為蘭德公司AI領域的研究報告和備忘錄,余下14篇為相關專著、業內專家手稿、哲學和心理學文獻,其中涉及哲學和心理學的文獻是:
(1)笛卡爾:《談談方法》;
(2)完形心理學創始人,德國心理學家Max Wertheimer:《創造性思維》;
(3)邁克·波蘭尼:《經驗和模式感知》,載于AI早期文集《心智建模》;
(4)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藍皮書和褐皮書》;
德雷大眾通過研究當時AI領域的主要學術論文,在序言和Part I對AI的進展進行了評估,他的主要結論是:
(1)由于當時新聞媒體的宣傳和AI科學家的樂觀主張,一些分析哲學家(Putnam、Scriven、Ziff)和神學家、倫理學家對機器大腦的立場雖然相反,但均錯誤地以為高度智能的人造物已經或即將被科學家開發出來,而這個并不是事實,因此需要對AI的研究現狀進行重新評估;
(2)在博弈、問題求解、語言翻譯和學習、模式識別這四個當時比較活躍,而且被公認為是人類智能才能勝任的領域中,AI研究都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包括國際象棋中的組合爆炸、啟發式方法在機器定理證明中的停滯、10年來投入了1600萬美元的機器翻譯面臨的上下文歧義問題、模式識別只能做到識別手寫的摩爾斯電碼(MIT林肯實驗室)和英文字母的水平。
接下來,德雷大眾從哲學和心理學方面來評價這些困難的深層次意義,并且是以一個比較積極的態度,“倘若人們正視否定的結果,那么該結果也是有趣的。遞減的進展代替了預測的加速成功,或許表明了未曾預料的現象。我們正在一個象速度那樣的連續體上推進嗎?當我們接近光速時,這樣的進展會越來越困難,或者相反我們是在面對一個非連續體,就象那個爬樹來登月的人?”,從這段原文可以看出,德雷大眾從一開始就未曾否定AI的意義,只是在質疑當時AI研究的主要假設和方法論。
德雷大眾主要是從人類與機器對信息加工形式的對比來闡述當前困難的深刻意義,他在Part II中列舉了四種:
(1)人類思維的邊緣意識與AI的啟發式搜索;
(2)人類思維的本質/非本質區分與AI的試錯法;
(3)人類思維的模糊容忍度與AI的窮舉;
(4)人類思維基于上述三種信息加工形式的明晰組合(Perspicuous Grouping)能力;
由此,德雷大眾得出了人類能在下述困難逐步加大的條件下進行模式識別的結論:
(1)模式可能歪斜、不完整、變形和在噪聲環境中;
(2)模式識別所需的特征雖然清晰甚至能形式化,但搜索難度會急劇加大(指數爆炸);
(3)特征可能依賴內外部上下文,從而不能從列表中隔離出來單獨考慮;
(4)可能沒有公共特征,但“重疊的相似性的復雜網絡”總能識別新的變化。
任何機器實現的模式識別能力,應與人類思維的能力等效,因此必須具備這些能力:對模式的特定實例把基本特征從非基本特征中區分出來、利用停留在意識邊緣的線索(或暗示)、.考慮上下文環境、把個體感知為典型,即把個體定位于一個范型實例。而目前AI在模式識別方面的困難,都給博弈、問題求解、語言翻譯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但是,AI科學家共同體并不這么認為,德雷大眾指出:“盡管有這些巨大的困難,認知模擬和人工智能的工作者卻并不氣餒。事實上,他們還毫無理由地樂觀。作為這種樂觀的基礎是人類信息加工必須按照象數字計算機那樣的離散步驟來處理的信念,而且因為自然用這種加工形式產生了智能行為,那么合適的編程應該能夠從機器導致這樣的行為。”這種AI研究者中的教條主義必有其根源,這種根源就是心理學上的聯想主義假設。
在Part III,德雷大眾認為沒有經驗和先驗證據支持聯結主義者的假定,因此也沒有理由期待AI領域的持續進步,機械式信息加工有內在限制,而人類卻沒有這種限制。他指出了采用認知模擬進路的若干主要威脅:博弈中事實的無限性和無限“進行”(Progression)的威脅、問題求解中需求的不確定性和無限退行的威脅、上下文相互作用和循環性引用的威脅。
在以上基礎上,德雷大眾把人類智能行為根據AI實現的可能性分為四類:聯結主義的、非形式化的、簡單形式化的、復雜形式化的,認為聯結主義和簡單形式化的行為可以用計算機模擬,而非形式化的行為難以模擬,復雜形式化行為僅在很小程度上可以模擬。他希望:“所有智能行為可以映射到多維度連續體的假設鼓勵AI工作者從兩個有希望的領域中的成功,推廣到另外兩個尚無事實性成功期望的領域。”
德雷大眾在Part III中的結論并不是否定性的,他指出:
(1)短期來看需要考慮人類智能和機器智能的協作,只有從長期來看非數字化的自動機才能表現出在處理人類非形式化世界中關鍵的三種信息加工形式;
(2)目前的困難和停滯并不意味著之前對AI的投入完全浪費,而是應該調整到聚焦三種人類獨特的信息加工形式上來。
在報告的最后,德雷大眾如此結尾:“如果煉金術士不再關注曲頸瓶和五角器皿,而把時間花在尋找問題的深層結構,如果人從樹上下來開始著手發明火與車輪,事情就會向一個更令人鼓舞的方向發展。畢竟,三百年后我們確實從鉛提取了黃金(也登上了月球),但這只有在我們放棄了煉金術水平上的工作,達到化學水平甚至更深層次的原子水平上后才會發生。[5]”
三、《煉金術與人工智能》的影響和AI的第一次冬天
德雷大眾的這篇報告在當時由于其觀點過于大膽,剛發布時反而沒有引起AI學者內部的大規模反應,出于對報告內容的擔憂,蘭德公司1965年僅以最低級別的備忘錄方式發布了油印版,1967年才發布了印刷版[6]。
當時對于這份報告大致有三種不同的傾向和態度,大致如下[7]:
首先是個別人的激烈反應,例如1968年1月麻省理工學院(MIT)的Seymour Papert發表了一份同樣言辭激烈的備忘錄(AIM-154):《休伯特·L·德雷大眾的人工智能:謬論種種》,其中他說道:“我得知反駁針對Simon的誹謗指控是不相干的,因為其他人確實已經對人工智能中的成就提出了錯誤的主張,也得知表明德雷大眾的解釋混亂是浪費時間:即為什么機器能下跳棋但不能下國際象棋是因為計算機翻譯俄語確實遇到了困難……我被告知他的觀點必須作為擁有深度‘人文主義’內容的文學想象作品閱讀。”
其次是雖然反對報告觀點,但表面上態度比較紳士和含蓄,甚至置之不理。例如德雷大眾直接攻擊的西蒙和艾倫·紐厄爾,還有Fegigenbaum和馬文·眀斯基,這也是AI共同體中大多數人的態度。例如,西蒙和馬文·眀斯基都不認可德雷大眾提出AI研究陷入停滯的觀點,他們并未在公共場合中表達此意見,而是在接受Pamela McCorduck的口述史采訪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西蒙在1957年做出的十年內AI在國際象棋和作曲達到人類水平的預言,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資金資源投入的問題,也就是這些問題的意義在AI中并不這么重大。眀斯基回憶說:“也許西蒙低估了國際象棋有多難,但我想他真正的失誤是另一個有趣的原因,因為他是管理學院的院長。西蒙的重大失誤在于他對有多少人從事國際象棋問題的估計上,當他做出預言時,我想他認為從那時起的三年或四年內,全世界有數百人非常努力地編寫國際象棋程序……麥卡錫偶爾關注此問題,把好問題分配給差生,我的實驗室則不鼓勵這樣。”
但是從多年后的口述來看,西蒙對德雷大眾這份報告的態度也是很激烈的:“……他在此前后與蘭德公司沒有任何聯系,也根本沒有相關技術背景,但他是蘭德公司顧問這個事實馬上給了他可信性……但我關于此事的不滿是蘭德的名字附加在這個垃圾上,這才真正是錯誤的炫耀。”就連蘭德公司的Paul Armer也不喜歡他,但同時也有一些人相當認可這份報告,Paul回憶說:“我認為這是糟糕的哲學……,我也不是哲學家,但我認為它不好。我與部門中喜歡此報告的其他人發生了激烈爭吵,他們用我自己關于檢查制度的聲明將我置于尷尬之地……”。同樣,Feigenbaum在多年后也如此說:“AI所需要的是好的德雷大眾,AI中的概念問題確實很粗糙……但是德雷大眾用他沒弄明白和過時的東西猛擊我們的頭……他提供給了我們什么作為代替?現象學!那是和絨線球、棉花糖一樣無價值的東西!”。
第三種態度就是對報告的基本立場持擁護立場,首先在蘭德公司內部就有不少人對報告內容認同,他們也迫使Paul Armer最終將之公之于眾,很快引起了AI共同體之外的廣泛關注,在沒有廣告宣傳的情況下,成為蘭德公司賣得最好的報告之一,德雷大眾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來信,1966年6月《紐約客》雜志還專門介紹了這篇報告,德雷大眾本人也因此報告被計算機科學共同體所接受,成為AI科學家不得不接受的一個事實。
接下來幾年德雷大眾的報告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其中一件事情是MIT的MacHack象棋程序擊敗了德雷大眾,對局結果印在了美國計算機學會(ACM)的人工智能專業組(SIGART)的公報上,西蒙對此寫了一封題為“冷靜!朋友!”的公開信作為對德雷大眾報告的正式公開回應,其中有一句這樣的表達:“……這是一場真正扣人心弦的比賽,其中一個人的邊緣無意識被另一個人徹底打敗…..”,邊緣意識是德雷大眾批判早期AI的核心概念武器,西蒙的公開信最終還是表明了AI共同體與德雷大眾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德雷大眾回憶當時MIT從事AI的同事:“不敢被人看見與我一起午餐”[8]。
《煉金術與人工智能》從事后來看對早期AI研究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方面1972年德雷大眾在報告基礎上進行擴充,出版了《計算機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極限》,這本書沿著報告的思路,不僅引用了更多的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文獻,而且也對眀斯基1968年出版的AI論文集《語義信息加工》中反映的最新進展進行了研究,把報告中的聯想主義心理學假設擴充為生物學、心理學、認識論和本體論四個方面的假設,從而涵蓋了當時AI研究方法的全部基矗
德雷大眾從報告擴充到專著的最根本變化在于他引入了海德格爾、梅洛·龐蒂關于軀體在知識獲取和應用中的作用,同時也用波蘭尼、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來批駁AI研究的假設,使得其論點更加富于建設性。
《煉金術與人工智能》在另一方面的重大影響就是與1966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ALPAC(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自動語言處理顧問委員會)報告,1973年英國科學研究理事會的LightHill報告一起,成為了AI歷史上第一次冬天(1974年-1980年)的主要標志。如果說德雷大眾的工作是因為其非專業出身而不被AI研究人員認可之外,而后兩者的專業學術背景帶來的影響力就直接導致了政府和軍方大規模削減甚至終止對AI的研究資助[9]。
ALPAC本身是由JALPG(Joint 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Group:聯合自動語言處理組)于1964年設立的,而后者是美國國防部、國家科學基金會、中央情報局三方為協調聯邦層面的機器翻譯研究而成立的組織,ALPAC的主席是當時貝爾實驗室的電子和通訊專家約翰·皮爾士(PCM:脈沖編碼調制的發明人)5。LightHill報告是英國科學研究理事會委托劍橋大學盧卡斯講席教授、物理學家James LightHill爵士對當時英國以AI研究現狀調查提交的一份獨立報告6。
ALPAC報告的結論是機器翻譯過于昂貴,比人工翻譯慢而且不夠準確,在較近的將來達不到人類翻譯的品質,因此只對兩個方面提供資助:將作為語言學分支的計算語言學當成一門純科學研究,以及對人工翻譯進行改進提高。LightHill報告的結論是僅支持對神經生理學和心理學過程的計算機模擬,而放棄對機器人和語言處理的資助,這導致了科學研究理事會終止對除愛丁堡、蘇塞克斯、埃塞克斯三所大學之外的其他大學AI研究的支持。
在1969年美國國會通過Mansfield修正案后,DARPA(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被要求資助面向任務的直接軍事用途的研究,而不再支持間接的基礎研究,其研究轉向了諸如自動坦克、戰役管理系統等具有明確目標的軍事項目,到1974年已經很難從DARPA申請到經費資助。1971年DARPA雄心勃勃在BBN、IBM、卡耐基·梅隆大學、斯坦福研究院啟動的語言理解識別(SUR:Speech Understanding Recognition)項目,至少包括1000個詞匯,希望能夠理解領航員的語音命令,但最終實現的系統只能聽懂按特定順序說出的詞句,DARPA對此很不滿意,于1974年取消了每年300萬美元的資助7。
無論德雷大眾的報告內容是否得到AI共同體認可,從導致AI第一個冬天的原因來看,他在1964年的工作相當準確地預見了當時在媒體上樂觀情緒背后的深層次危機,這些危機在十年之后的爆發迫使AI共同體更加包容地對待哲學家對機器智能方面的思考和立常
四、德雷大眾在《計算機不能做什么》后續版本的立場
1979年,《計算機不能做什么》第二次再版,德雷大眾持續跟蹤了1972年之后的AI進展,并為此寫了一個長達70頁左右的第二版序言,其基本立場是認為他在第一版中的看法與之后的AI發展是相符合的[10]。
德雷大眾把1967年到1977年之間的AI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67年到1972年,稱之為“控制微世界”,主要針對Terry Winograd用于處理積木世界的自然語言理解程序SHRDLU和斯坦福研究院的Shakey機器人項目提出了異議,認為認知過程的原理仍未取得重大進展,類似于積木這樣的微世界,不能逐步逼近復雜的真實世界,Shakey項目反而導致了機器如何獲得知識并予以表達和應用的難題,尤其是真實世界的常識知識問題。他說:“認為這種無盡頭的、對人類其他實踐活動的參照將會收斂起來,從而能對簡單的微世界做相對孤立的研究,這種完全不合理的信念反映了一種要把在自然科學領域已取得成就的方向搬到AI中來的天真想法”。
第二個階段從1972年到1977年,主要聚焦當時取得一定成功的專家系統,例如MYCIN,并分析了眀斯基對知識表達的框架理論和香克的腳本理論的局限性,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人類智能難以在脫離其上下文環境及其局勢的情況下,單獨地表示出來和加以理解,并在AI中予以實現。
1992年,德雷大眾出版了《計算機不能做什么》的第三版,但書名改成了《計算機仍然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新的版本并沒有修改正文,但增加了一篇約50頁的新序言,在該序言中德雷大眾與時俱進跟蹤并評估了四類不同的AI研究策略,第一類仍然是符號主義的,以1984年由Lenat啟動的Cyc項目為代表,該項目試圖組合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識知識的本體論和知識庫,從而使計算機達到人類推理的智能水平,這是AI知識工程研究進路中最為宏大的項目,至今仍以OpenCyc的開源項目方式進行。其他三類分別是MIT人工智能實驗室以海德格爾現象學為基礎開發的交互式人工智能(海德格爾式AI)、80年代后復興的神經網絡建模和強化學習[11]。
在上世紀90年代初,AI的研究進路已經出現了更加多元化的場景,德雷大眾承認AI這方面的進步,但仍然捍衛人類理性和智能的獨特地位,這種獨特性來自于軀體、社會和文化,“我們的需要、渴望和情感借由關于我們行為適當性的感覺直接呈現給我們。如果這些需要、渴望和情感輪流依賴于被社會化到文化中的生物軀體的能力和弱點,那么即使強化學習策略仍有很長的路要走。[12]”
五、德雷大眾對AI發展的主要影響
人工智能這個名詞雖然是在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上由麥卡錫提出,但關于這個學科的理論和實踐探索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戰前的圖靈和維納。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基本不加區分,一直到1973年LightHill報告中才由英國認知科學家Longuet-Higgins提出“認知科學”這個名詞,但當時人工智能與認知科學的區分仍不明顯,這種情況要到1975年提出認知科學支撐學科的六邊形模型后才改變[13]。
但是到今天為止,對于AI的定義,仍然存在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在《MIT認知科學百科全書》的序言中,將傳統AI當成計算智能:
“有兩種互為補充的人工智能觀:一種是作為關注智能機器建造的工程學科,另一種是關注對人類智能進行計算建模的經驗科學。在該學科早期,兩種觀點很少得到區分。其后根本性的分歧出現了,前者主導著現代人工智能,后者是許多現代認知科學的特征。基于這個原因,我們采用更為中性的術語‘計算智能’作為本文標題——兩個共同體都使用計算術語來處理智能理解的問題。[14]”
美國人工智能學會(AAAI)對AI的定義也小心翼翼地維持兩種人工智能觀的平衡:“對作為思維和智能行為基礎的機制的科學理解及它們在機器中的具身實現8”,但大多數AI學者還是從狹義來理解AI,例如麥卡錫的定義是:“制造智能機器的科學和工程,特別是智能的計算機程序,它與利用計算機來理解人類智能的類似任務有關,但不必自我限制于生物學上可觀察的方法。9”
在目前流行的AI教科書《人工智能——一種現代方法》對AI的定義是:“理性智能體的設計過程……著重討論理性智能體的通用原則以及構造此類智能體所需的組成部分”[15],這里強調的是一種工程和實踐意義上的人工智能觀。
為什么對AI的描述仍然存在這些分歧,這里無疑和早期AI的研究綱領的單薄和宏大抱負、樂觀預言的失敗有關,德雷大眾的蘭德報告起到了導火索作用,使得在70年代初之后AI在美國和英國的聲望空前下降。
德雷大眾不僅促使公眾、政府機構等利益相干者重新審視AI,而且始終運用德-法傳統的大陸哲學思想來為最新的AI研究開方抓藥,包括:
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意向性理論;
波蘭尼、龐蒂關于軀體在知識獲取和人類行為中如何發揮作用的理論;
海德格爾關于在世存在、上手、預備上手等一系列存在論現象學的觀點;
對于早期AI中過于簡單的認識論假設,對人類智能行為的不恰當的模擬,德雷大眾也引用了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和其語言哲學方面的觀念,他的這些工作至少從兩個方面對AI的歷史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影響了AI工作者的研究實踐,特瑞· 溫諾格拉德(TerryWinograd)不僅把海德格爾哲學引入到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的課堂上,甚至在MIT的人工智能實驗室,80年代后也轉向了德雷大眾提出的研究方向, “對那些追隨人工智能歷史的人來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會成為‘海德格爾式的人工智能’的搖籃。正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德雷大眾首次明確表達了他的批評,而20年來人工智能實驗室的智識氛圍(intellectual atmosphere)對承認他言論中的含義明顯是敵對的。盡管如此,該實驗室現在完成的某些工作似乎受到了海德格爾和德雷大眾的影響。[16]”
對于認知科學從符號-計算-表征為代表的早期研究綱領向當前以涉身-交互-情景為代表的研究綱領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德雷大眾當然不是推動這種轉變的唯一代表,作為現象學大家和人工智能哲學研究的旗手,他開啟了一個批判的潮流,在其之后,塞爾、Haugeland、丹尼特等人不斷挑戰GOFAI的形式化、認識論上人與世界的分離觀點、事實的離散性和原子性等核心觀念。
六、結論
作為一名沒有受過控制論、信息論和計算機專業訓練的哲學家,德雷大眾用這篇報告闖入了AI學術共同體的核心領地,并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建議,在哲學的認識論轉向、語言轉向之后,也影響了哲學的心靈轉向,某種程度上弱化了人們對認知科學將要消解傳統認識論的擔心。同時,對于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這樣研究人類自身心靈和思維能力的工程學科和交叉學科,為傳統哲學與這些新興尖端學科的對話提供了一個正面示例,因為德雷大眾并不是象倫理學家、神學家那樣捍衛傳統的人類中心論的人文價值,而是從認識論、形而上學方面來挑戰AI的研究方法基礎,不管AI科學家共同體中的部分成員從一開始如何封閉和敵對,最終還是從外部打開了一扇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交流的窗戶。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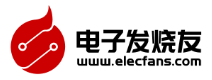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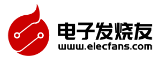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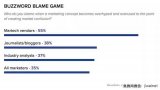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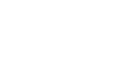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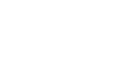





評論